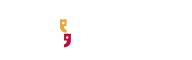專題文章:男性婚姻暴力加害人的羞恥感、罪惡感、歸因型態及婚暴行為之關係(一) 緒論
次閱讀
強尼戴普,安柏赫德世紀訴訟案甫告一段落,快來認識婚姻暴力,親密伴侶暴力。根據張銘倫臨床心理師在男性關懷專線和審前鑑定的經歷,男女互毆並不少見,除互控傷害之外,通常只有肢體較為弱勢,或心理較受威脅的一方會申請保護令;而申請了保護令,也未必會拿來當作離婚的籌碼,有時藉由社會控制的力量,雙方得以井水不犯河水、相安無事一段時日。要研究「衝突升高」到「暴力」這之間的過程,必須知道暴力行為發生之前,有哪些影響因素間接或直接的促使暴力行為的發生,如此才有機會加以避免、防範,或是調節相關因素的影響,使暴力傷害降至最低。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婚姻暴力是存在已久的問題,但是以往總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使得暴力行為普遍存在於家庭中,卻難以介入。國內於民國八十七年通過「家庭暴力防治法」,將「家庭暴力」定義為「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
婚姻暴力屬於家庭暴力中的一部分,法規的施行使得家庭暴力防治開啟曙光,也使婚暴行為從關起房門的家務事正式浮出檯面。然而,研究與輔導治療常將焦點放在受害者身上,若對加害人的心理歷程多加探討,找出暴力行為的預測因子,不但增進對暴力行為的生成和影響的了解,對於矯治工作的方向也將有所拓展。
根據內政部統計(內政部統計資訊,2008),民國94年警察機關受理家庭暴力案件27,548件,較民國93年增加5,368件(增加24.20%),而近五年警察機關受理家庭暴力案件呈現逐年增加趨勢。民國95年全國婚姻暴力的通報案件有41517件,占所有案件類型62%,民國96年全國婚姻暴力的通報件數比去年增加2271件,總件數占所有案件類型60%,可見家庭暴力是日益嚴重的問題,婚姻暴力的通報件數幾乎占家庭暴力案件的一半以上,足見其份量。
若以性別來觀察,民國96年男性加害人比例占82%;依年齡層來觀察,成年男性加害人比例占78%,暗示婚姻暴力在家庭暴力(Domestic Violence)中佔有很大的成分,且加害人以男性居多。國內研究調查也顯示,妻對夫的暴力行為主要以「妻因受虐而反擊之暴力行為」的形式顯現(劉宏恩,1998),因此可知,男性加害人為行使暴力行為的主要發起者。
Walker(1984)根據行為增強(behavioral reinforcement)和壓力消減(tension reduction hypothesis)的概念,提出暴力循環的三階段論(The three-phase violence cycle)來說明暴力關係的維持、週期性存在。由此可知,婚姻暴力常會循環發生,肢體傷害一再重複,足見其嚴重性。Walker試圖爲暴力關係的維持做出解釋,所提供的治療介入角度也放在如何替女性「賦權」(reempowerment)。
以往研究多將重點放在婚姻暴力對婦女的影響(陳若璋,1992;沈慶鴻,2000;趙葳,2002;吳柳嬌,2004;Hsieh et al.,2009)、受害婦女因應方式(鄭瑞隆、許維倫,1999)、婚姻暴力對幼童的影響(曾慶玲、周麗端,1999;楊倩蓉、連廷嘉,2009)以及社政或警察對婚姻暴力之處理(黃富源,1995;黃翠紋,2002;王樂民、鄭瑞隆,2008),然而,若能對婚姻暴力犯的特質多加了解,可彌補目前多數方案「以一應全」(one-size-fit-all)之疏漏,有利於深入介入與治療(林明傑、沈勝昂,2004)。
婚姻暴力犯罪和暴力犯罪或其他種類犯罪,有何不同之處?雖然國內已經對家庭暴力的問題立法保護受害人,公權力對此家內事有介入和執行的地方,但是此種犯罪性質的探討仍然不深入,大部分為流行病學般的描述統計分析(陳筱萍、周煌智、吳慈恩、黃志中,2004),或是質性研究(李宜靜,2001;陳高德,2003;林裕珍,2006;陳怡青、楊美惠,2007)對少數案例探討,卻缺乏大量實徵資料去支持對心理現象的討論,縱然有量化研究,受訪者卻是受害人(林明傑等人,2007),不知結果能否在加害人身上驗證。針對加害人心理病理層面進行研究,有助於衡鑑與治療,尤其認知功能的探討更為重要,有助於對後續情緒與行為的改變。
婚姻為家庭的開始,婚姻中存在許多壓力和難題,但是溝通或調適的功夫做得不好,一方選擇用暴力行為來因應心理壓力或解決困難或衝突,只會衍生更多問題,這場婚姻的雙人協奏曲便開始走調。
在引發暴力之前,通常雙方已經經歷長時間無法解決的衝突,並且進入某種程度的緊張關係(Walker, 1979;盧昱嘉,2000;陳高德,2003)。陳若璋(1992)研究55名被毆婦女,採事後回溯方式,想了解婚姻暴力如何開始,發現婚姻暴力起於婚姻惡化之後。如何疏通或掌控婚姻關係中的衝突不至於演變成婚姻暴力,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
要研究「衝突升高」到「暴力」這之間的過程,必須知道暴力行為發生之前,有哪些影響因素間接或直接的促使暴力行為的發生,如此才有機會加以避免、防範,或是調節相關因素的影響,使暴力傷害降至最低。
過去對於暴力行為的影響因素研究方面,有研究者將重點放在自我意識情緒對攻擊行為的影響(Tangney, 1990, 1992a;1996;Thomas, 1995;Herr, 2001;吳孟芳,2006;丁耕原,2008),自我意識情緒指的是以自我評價或自我反映(self-reflection)為主的情緒感受,這樣的情緒包含羞恥感、罪惡感、尷尬(embrassment)、自豪(pride)(Tangney, 1999)。
Tangney(1996)的研究結果指出,生氣、憤怒表現與羞恥感傾向特質之間的相關程度相當的穩定,它幾乎橫跨不同的年齡層,從小孩、青少年、以致於到成年人都有顯著的關係。而罪惡傾向和建設性的處理生氣有關,包括建設性的意圖、修正的行為、和生氣目標非敵意的討論、對目標角色的生氣評估和正向長期的結果。
Tangney因此認為,和一般族群比較起來,當生氣來臨時,差恥感傾向特質的個體傾向採用不適應的、沒有建設性的反應來回應生氣,而這些不懷友善的念頭可能包含有邪惡、怨恨的意圖,包括直接或間接、替代性的攻擊暴力。
Tangney因此推論,有差恥感傾向特質的個體應該比較容易受到憤怒的牽引,進而出現攻擊的行為;另外,相較於罪惡傾向個體,羞恥傾向者比較不容易表達生氣,會出現間接的攻擊,例如,自我攻擊、忍住發怒,但在衝突情境中,羞恥傾向個體會出現較多的主動攻擊(肢體、口語行為),可能是羞恥傾向個體常以順從或被動的方式去經歷憤怒,而出現非理性且產生不良後果的生氣表達方式。
羞恥感和婚姻暴力有正相關(Dutton, 1995;Dutton, Ginkel, & Starzomski, 1995;Retzinger, 1991;Scheff, 1995;Scheff& Retzinger, 1991;Eisikovits & Enosh, 1997;Hooper, 2002;Simon, 2002;Brown, 2004);而「同理驅動的罪惡感」(empathy-driven guilt)可以抑制婚姻暴力的發生(Eisikovits & Enosh, 1997)。
吳孟芳(2006)以男性婚暴者為對象,測量其罪惡感、羞恥感、同理心和憤怒攻擊之間的關係,目的是想瞭解罪惡感、羞恥感和憤怒攻擊的關係,是否在婚暴男性加害者族群身上找到驗證,結果僅獲得部分支持,婚暴者的羞恥感並無顯著高於一般人,羞恥感無顯著預測婚暴危險度,而且觀點取替能力愈高,婚姻暴力危險程度反而卻愈高,研究者認為可能是婚暴者認為自身具有觀點取替能力,但是無法運用於婚姻中的衝突事件。由此可懷疑,婚暴者對一般生活事件和婚姻關係事件的認知歷程可能有不同。
是什麼樣的認知元素在調節或是中介罪惡、羞恥感對攻擊暴力的影響,本研究假設歸因方式為其中影響因素,Herr(2001)研究大學生發現歸因型態和羞恥感、生氣有關。許多國內外學者發現,男性婚暴加害人對婚姻關係中重要事件的解釋,會影響衝突發生的機率(Holtzworth-Munroe & Jacobson, 1985;Fincham & Bradbury, 1987;Fincham & Beach, 1988;Tonizzo、Howells、Day、Reidpath & Froyland(2000)李良哲,民86;王行;1998;李宜靜,2001;鄭秀津,2003),若加害者願對自己的暴力行為負責的話,將可能比那些責備妻子或情境因素的人有動機去尋求協助,同時,在施暴後也會對自己的暴力行為感到後悔或抱歉,即罪惡感反應(李宜靜,2001)。因此,男性婚姻暴力者的罪惡感、羞恥感傾向和歸因方式是本研究的探討重點。
婚姻關係中的歸因型態 (Attributional style),此議題獲得國外研究者許多關注,有許多研究探討歸因或解釋生活事件的方式和婚姻品質或是婚姻滿意度的關係(Madden&Janoff-Bulman, 1981;Fincham, 1985;Holtzworth-Munroe&Jacobson, 1985;Fincham&Bradbury, 1987;Fincham&Beach, 1988;Holtzworth- Munroe & Hutchinson, 1993;Horneffer & Fincham, 1995;Davey, Fincham, Beach, & Brody, 2001),國內訪談研究發現加害者有自利歸因偏誤(鄭秀津,2003),且將婚暴責任歸咎妻子(陳高德,2003;潘美玲,2006),對妻子的行為意圖做負向的歸因時,會增加其攻擊的危險性(李宜靜,2001;鄭秀津,2003)。
Tonizzo等人(2000)發現有肢體暴力比無肢體暴力的男性,更會把伴侶的負向行為歸因成穩定的、故意的、自私的和該被責備的,然而,也有研究發現婚姻暴力與不適應的婚姻型態並無顯著相關(Fincham、Bradbury、Arias、Byrne & Karney, 1997)。
Byrne和Arias(1997)預期負向的歸因方式會使婚姻痛苦預測肢體暴力的效果達顯著,結果發現責任歸因可以調節婚姻滿意度和肢體暴力之間的關係,但只發生在妻子身上,丈夫並無發現此調節的影響。
本土研究中直接探究其中關係的量化研究為數不多。李良哲(1997)發現婚姻衝突情境的認知評估,會透過人格特質或婚姻滿意程度的作用,間接影響婚姻衝突的因應行為。王行(1998)觀察到已婚男性有自利偏誤的傾向,對婚姻關係所發生的重要事件的體驗與解釋,若是較自我中心(以自己為導向,自己的價值、自己的立場、自己的角色或自己的責任視框為出發),容易產生與配偶相對的感受;而較具有同理心(以雙方的立場為視框出發)者,則能減少誤會及衝突,產生對配偶了解的體諒感受。
陳筱萍等(2004)發現婚姻暴力者所呈現的精神病理符合精神科診斷的比例不高,少有嫉妒意念/妄想,而是以衝動性、認知偏差與不當飲酒居多。由此可知,認知因素在婚姻衝突扮演重要角色,但對於是什麼樣的解釋風格或歸因型態影響婚姻關係卻沒有更多聚焦。
在不同之情境下,個體是否有相同的歸因型態,也是研究者感興趣的問題(Kelley, 1967;Abramson, 1991)。人在一般的生活事件當中或許能理性判斷事件成因,然而婚姻是兩個家庭的結合,不同的家庭教養出不同性格的孩子,面對婚姻生活中的特定事件便可能勾起不同的情緒反應、因應模式甚至是特定的認知評估方式,也就是男性加害人面對家庭或婚姻生活,可能出現有別於面對日常生活的歸因型態,根據內政部調查報告指出,許多加害人只在家中施暴,在其他的社交場合卻可能是非常溫文有禮,言行有分寸的人。
國內外研究發現,加害人凡事外在歸因、責備他人(周月清,1995;陳筱萍等2004;Walker, 1979),但陳筱萍等(2004)發現家庭暴力相對人所呈現的精神病理符合精神科診斷的比例不高,少有嫉妒意念/妄想。若凡事都外歸因,可說是呈現一種穩定的認知評估傾向或特質,甚至大膽推論此為婚姻暴力成因的其中一病理因素,但是有些加害人仍會將問題歸因為雙方或自己,甚至不同的歸因內容會有不同的歸因型態,例如,將「溝通困難」歸因於雙方的責任,「打人前喝酒」歸因於自己,「聲請人有外遇」則歸因於對方。所以,歸因型態是否具有情境的一致性,是否「凡事」將責任外推,仍有待澄清。
因此發展和使用特定情境的測量工具,可更敏感地測量出屬於該情境特有的歸因型態,面對一般生活事件的解釋風格與和衝突內容相符合的特定事件之歸因型態是否相同,在特定事件當中何種歸因型態容易傷害關係,是本研究關心的議題。
本文編輯與作者 張銘倫臨床心理師
- publisher:
- 聊聊心理治療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