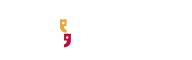專題文章:港湖女神立委高嘉瑜遭男友家暴,親密伴侶暴力要注意的事
次閱讀
「衝突升高」到「暴力」這之間的過程,瞭解哪些因素間接或直接的促使暴力行為的發生,才有機會加以避免、防範,使暴力傷害降至最低。羞恥感和罪惡感皆為自我意識情緒中的一種,相較於羞恥感是「他的錯」的「見笑轉生氣」,罪惡感是建設性的自責,並有動機性的修補行為。歸因型態是解釋或是回答一個事件爲什麼發生的不同向度評估,愈將感情中的負向事件歸因於伴侶內在、穩定、全面、伴侶故意、伴侶自私、伴侶該被責怪,可能暴力程度愈高。張銘倫(2009)研究歸因型態與自我意識情緒-羞恥感、罪惡感對婚姻暴力是否有調節效果,發現採他責歸因者,若羞恥感愈低,婚姻暴力程度愈低。面對施暴者時,治療者除了釐清和標定出他責歸因型態,還要協助覺察和思考行為背後被羞恥感摧毀的面子、脆弱的自我概念和價值感,女友和前男友聯絡,是否聯想到「藕斷絲連」、「紅杏出牆」、「戴綠帽」、「不把林北擺在眼裡」、「愛前男友比愛我還多」、「性能力被得不到的前任擊敗」...等等中介思考,甚至探索原生家庭、成長過程的創傷經驗,執行深度心理治療。
「衝突升高」到「暴力」這之間的過程,必須知道暴力行為發生之前,有哪些影響因素間接或直接的促使暴力行為的發生,如此才有機會加以避免、防範,或是調節相關因素的影響,使暴力傷害降至最低。
自我意識情緒: 羞恥感、罪惡感與親密伴侶暴力
羞恥感是自我意識情緒中的一種,當個體面對道德相關事件違反內化的標準時,所產生的負向情緒狀態,包含自我專注(self-focused)的痛苦經驗,還有無價值、無能力感或自我輕視的感受,也將為個體帶來極度嚴厲的自我評價(self-evaluations) 。
罪惡感是自我意識情緒中的一種,是適應性且具有建設性的道德情感(moral affect),當個體面對道德相關事件違反內化的標準時,伴隨緊張、自責的懊悔感受,個體將產生動機性的修補行為。
歸因型態是解釋或是回答一個事件爲什麼發生時,用內外在(locus),穩定性(stability)和全面性(globality)、故意向度、自私向度、責怪向度等向度來描述造成事件的原因。愈將感情中的負向事件歸因於伴侶內在、穩定、全面、伴侶故意、伴侶自私、伴侶該被責怪,可能暴力程度愈高。
很多研究是探討羞恥感和親密伴侶暴力的關係(Dutton, 1995;Dutton, Ginkel, & Starzomski, 1995;Retzinger, 1991;Scheff, 1995;Scheff & Retzinger, 1991;Brown, 2004),Dutton和其同事(1995)研究童年早期的羞恥感和長大後的親密伴侶暴力有關。Scheff和Retzinger(1991)描述婚姻爭吵中,因羞恥感而起的憤怒(shame rage)之循環。
Brown(2004)認為應以治療親密伴侶暴力加害人的羞恥感來改善親密伴侶暴力的問題,例如,讓治療者去接受、包容(containing)加害者的羞恥感,或是協助加害者確認出羞恥感受後,運用情緒和行為管理技巧轉化之。
Miller(1985)提出羞恥感與憤怒之間關係的兩個路徑,一是憤怒之後感到羞恥,二是羞恥感引發憤怒,這似乎可以說明,在婚姻暴力的懺悔期,男性常感到羞恥,但其實暴力循環仍然存在(Walker, 1979;Simon, 2002)。Simon(2002)發現暴力組的羞恥感和同理心有正相關,顯示婚暴的悔改期是被「羞恥驅動同理心」(shame driven empathy)所引發,而不是真心想補償、修復。
Eisikovits & Enosh(1997)不區分羞恥感和罪惡感,而是統一以「道德情緒」去看待,利用現象學研究,深入訪談20位男性婚暴加害人及其伴侶,想了解一、婚姻暴力在什麼樣情況下會產生道德情緒?二、道德情緒是否發展成婚姻暴力,其影響路徑的因素是什麼?結果發現,婚姻暴力之後會不會產生道德情緒,有幾個重要元素:第一,當事人否認或承認暴力行為;第二,當事人否認或接受暴力責任;第三,內在價值或理想和現實自我是否產生衝突;第四,是否有責難他人(accusatory others)的存在。其中,內在衝突和責難他人的存在,為產生道德情緒必要的前提條件。
道德情緒會不會發展成暴力事件的結果?要看當事人的前置狀況、覺察、選擇、對暴力事件和責任的否認與否,還有是否產生內在衝突。
前置狀況是伴侶帶了什麼東西進入歷程當中,例如,心理的、關係的、情境的、社會結構的。
內在衝突和責難他人,會影響暴力事件後是否產生道德情緒,暴力事件本身較無影響。
覺察和選擇不能分開,個體的覺察程度,以及選擇的覺察程度和反應(例如,對道德情緒的真實反應和解決方法),對暴力事件和道德情緒的否認與否,會影響暴力的後續發展。以上情況帶來包含五種路徑的模型,說明後續發展。
路徑一,日常衝突發展出道德情緒,當事人有高自尊、一般性羞恥感(normal shame)、想要補償的罪惡感、同理心,有能力解決衝突,就較不可能發展成暴力。這些資源不可得時就有高機會產生暴力。
路徑二,暴力後沒有道德情緒:個體沒有內在衝突和覺察,道德情感被壓抑成負向感受(bad feeling),容易投射到伴侶身上。
路徑三,道德情感的正向解決方式:如果一般性羞恥感(normal shame)和同理性罪惡感(empathy based guilt)讓個體經驗到補償的需要,就會有正向的反應結果,伴侶會有真正和可靠的反應,以建設性的方式來解決問題。
路徑四,不願承認道德情緒:伴侶會持續經驗莫名的負向感受(bad feeling),會藉由將責怪投射到對方身上來處理這種情緒,衝突漸劇。此路徑和路徑二的差別在於,路徑二的道德情緒是被棄絕的,完全覺察不到。
研究者引述一段例子說明,路徑四當中的伴侶會想復合,但只是為了恢復被暴力破壞的現狀,但否認道德情緒,會將兩人帶往肢體暴力的循環。
路徑五,覺察並有真正可靠的道德情緒:若能有覺察,會經驗到道德情緒的緩和,真正想要解決問題,不會讓不滿累積或擴大。
歸因型態與親密伴侶暴力
歸因導致責任的判斷,再造成責備,責備是造成婚姻關係痛苦的決定性因素(Fincham & Bradbury, 1992)。婚姻關係不佳的配偶容易將對方行為原因歸咎於個人化的、穩定、全面性,也容易將對方將行為意圖或動機歸因為有意的、故意的(intent)、自私的(selfishness)、應該被責備(blame)(Fincham & Bradbury, 1992)。有研究在婚姻暴力男性身上找到這些歸因型態(Tonizzo et al., 2000),但也有研究並無發現相關(Fincham, 1997)。
Horneffer 和 Fincham(1995)研究歸因向度的跨情境性,發現用「關係歸因測量」(RAM)測得的歸因向度與夫妻的婚姻滿意度和憂鬱分數呈現相關;也就是,愈內在、穩定和全面性的歸因,與夫妻的婚姻滿意度顯著負相關,與夫妻的憂鬱分數顯著正相關,但是,只有部分用「歸因型態問卷」(ASQ)所測得的歸因向度(穩定性與全面性)與丈夫的憂鬱有顯著正相關,與丈夫的婚姻滿意度無關。以丈夫的資料來看,ASQ的歸因型態分數僅能測得與丈夫的憂鬱相關,而RAM的歸因型態與丈夫的憂鬱和婚姻滿意度有關,可能對丈夫而言,ASQ與RAM分別表現出丈夫的不同心理狀態。
羞恥感、罪惡感、歸因型態與親密伴侶暴力
張銘倫(2009)想研究歸因型態與自我意識情緒(羞恥感、罪惡感)對婚姻暴力是否有調節效果,發現採他責歸因者,若羞恥感愈低,婚姻暴力程度愈低。
一般組的婚姻不適應歸因(他責歸因)可以預測婚姻暴力,婚姻不適應歸因愈高者,婚暴程度愈高,而羞恥感低的高不適應歸因者,婚姻暴力程度卻降低了,顯示羞恥感的作用之下,讓歸因預測婚暴的方向性改變,因此較支持羞恥感為歸因預測婚暴之間的調節變項,但此影響只在一般組身上發生,可能原因有幾個,一為羞恥感在一般組身上較容易運作,一般組的道德感較強,在乎他人的想法,羞恥感特質也較容易顯現。
二為一般組對於歸因的概念較容易理解,平常也有歸因思考的習慣,所以當婚姻衝突發生後,一般組清楚知道自己為什麼生伴侶的氣,再加上羞恥感特質的運作,引導出後續的因應行為,也影響婚姻暴力行為的發生。
三為一般組不像婚暴組一般,已經被認定具有犯行,所以一般組反而能在問卷上自由展現對婚姻衝突事件的看法,進而在一般組身上發現羞恥感和歸因之間的交互作用,這也可能是一般組和婚暴組在羞恥感無顯著差異,卻在分組之後以及在歸因的作用之下,讓一般組的羞恥感發揮影響力的原因。
張銘倫(2009)研究發現,罪惡感對婚暴者具有降低婚暴發生機會和嚴重性的作用,如何在婚姻衝突發生之後,有效引導出婚暴者的罪惡感,停止暴力繼續發生的循環,是一個可以考量的方向。但歸因型態似乎在婚暴組身上無明顯影響,意味著對婚暴者作認知的調整可能成效不彰,也可能婚暴者較少有歸因的習慣,需要治療者帶領加害人去探討自身對伴侶的歸因型態為何,讓加害人積極覺察對伴侶習慣作何種不適應於婚姻生活的歸因,才有可能評估歸因型態對婚暴行為的影響。
另外,研究限制是,婚暴組為受裁定保護令者,其可能自認為犯人,而且幾乎皆已經接受認知輔導教育,也可能引發其罪惡感以及使其不適應歸因較不強烈,未來相關研究應收取進入保護令審理程序,但尚未受裁定保護令者為佳,以排除認罪及認知輔導教育之影響。
歸因型態在婚暴者身上的意義不若一般組大,也可能和婚暴者表達與自我相關的內在衝突困難有關,而自我衝突的表達和自我概念的清晰度相關聯(Tonizzo et al., 2000),未來研究或可加入自我概念方面的測量,作進一步相關探討,使婚姻暴力的歷程模型更加周延。
在一般組身上較清楚看出羞恥感和歸因型態的影響,羞恥感在Tangney的定義裡面,為當事人常伴隨自我貶損的感受,對社區中有婚姻困擾而欲尋求協助的人來說,心理治療當中若能處理當事人羞恥感這部份,再加上評估婚姻生活中對伴侶的負向歸因,並加以調整,將可預防婚姻當中由摩擦衝突演變為嚴重的暴力行為,達到初級預防的功效。
研究限制還有,因收案資源和時間有限,未能將一般組與婚暴組加以配對,建議未來進行類似組間比較的研究時,先將婚暴組樣本收取完成後,再依照婚暴組特性收取一般組樣本,較能控制其他因素之影響。另外,若能獲得婚暴組穩定的樣本來源,建議對樣本分組,如,接受認知輔導教育之前樣本、接受認知輔導教育中的樣本、接受認知輔導教育後的樣本,甚至是僅收剛接受保護令審理的個案,才能確保樣本性質和研究結果最能貼近婚姻暴力現象的本質。
名人遭受親密伴侶暴力,對我們的啟示?
所以,面對施暴者時,治療者除了釐清和標定出是否有他責歸因型態,還要協助覺察與思考行為背後被羞恥感摧毀的面子、脆弱的自我概念和價值感,女友和前男友聯絡,是否聯想到「怎麼跟我在一起還想著別的男人?」「藕斷絲連」、「紅杏出牆」、「戴綠帽」、「不把林北擺在眼裡」、「愛前男友比愛我還多」、「性能力被得不到的前任擊敗」...等等中介思考,留存親密影片的動機是否想藉此控制女友? 帶著威脅性的感情還能深化彼此的信任感和親密度嗎?除討論眼前壓力衝突事件,也可進一步探索原生家庭、成長過程的創傷經驗,執行深度心理治療。
本文作者 張銘倫,聊聊心理治療所院長
- publisher:
- 聊聊心理治療所
-